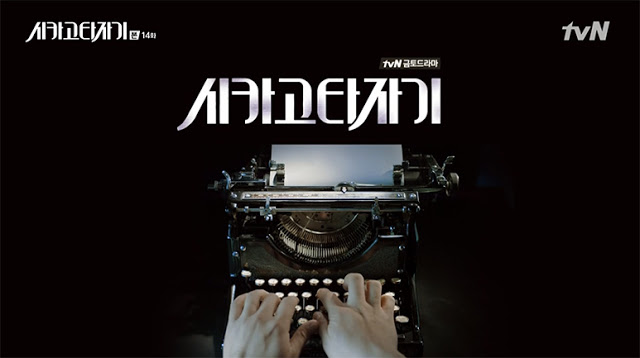去年底夥伴找我一起翻譯這本書,我一收到她寄來的檔案後就就對這次的案子非常感興趣,畢竟內容和插畫史有關,書中又放了大量的植物插畫,我的第一直覺認定這是一本容易上手的書(因為從事藝文翻譯工作的關係,所以我過去對版畫、水彩等技法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而且邊翻譯邊看漂亮的植物插畫,怎麼想都覺得是很夢幻的工作呀!因為這些原因,所以希望當時非常期待開工。
等到我實際開始翻譯以後,才發現原先以為的優點原來都是陷阱呀!從書名可以發現這本書的重點之一是「科學」,內容側重植物的生長史以及書中的主角「植物繪師」對於植物生長過程的觀察。植物繪師這個名詞其實是和我合譯的同事費了很多心思想出來的,希望能跟一般的「插畫家」有所區別,因為在攝影術發明以前,繪畫就是記錄歷史最直觀的方式,而植物研究當然也需要有專人負責記錄,這些「繪師」是為舊時代的植物留下直接觀察紀錄的功臣,以「繪師」稱之更能符合他們的工作態度與精神。(同事非常注重中文的用字遣詞,在這次的合作中我也從她身上學到很多東西,非常感謝她!)
而植物科學固然客觀,但科學研究往往不是一開始就能得到正確解答,從採集植物、保存到製作標本,這些前置工作的每個環節一旦出錯,或者繪師(經常身兼科學研究者)的主觀判斷失準,那麼插畫與其註腳當然就會跟著錯下去了,這樣的失誤對後世的研究者也會有連帶的影響,程度或小或大。(至於錯誤究竟會出在哪裡,又對研究人員有何具體影響?作者在書中提供許多的考據與例證,這些就請大家翻開書本一探究竟囉。)
翻譯本書遇到的挑戰之一:知識面
每次介紹新譯作時都會談到翻譯過程的挑戰,這次當然也不例外。要論嘔心瀝血,以我目前的經歷來看,這本書絕對名列前茅。
書中花了很多篇幅談了植物插畫從製備標本到付梓印刷之間的各個工作環節,而書中的很多作品其實都是以版畫技術製作而成,雖然我對版畫印刷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標本製備可是一竅不通,需要從頭了解。
生物學的相關知識也很重要,因為書中的插圖鉅細靡遺,有時描繪出孢子囊的結構以及繁殖過程各個階段的結構變化,有時討論了矽藻多元的架構,這些內容都需要額外尋找參考資料才能準確翻出相關資訊。
另外本書以西方尤其歐洲的植物為大宗,很多物種在台灣甚至沒有正式譯名,所以翻譯時也必須選擇一個符合科學命名方式且好懂的名稱,在這方面我也花了很多心思。針對有中文名稱的植物,也必須確認是中國用法抑或台灣用法(這裡已經不是政治問題,是科學研究精準度的問題了),也要確定這些中文是民間俗名抑或正式的中文名稱,因為有時候同一俗名可以套用在很多不同的植物身上。
翻譯本書遇到的挑戰之二:技術面
雖然本書的作者對科學插畫史做了很多功課,但有時語句較為破碎,句子前後不連貫,需要英文讀者自行腦補很多缺漏。但以我們在校受過的專業翻譯訓練來看,我會希望盡量把內容寫得清楚、易懂,即便原文不好懂,譯文也要盡量降低讀者的認知負擔(口譯的重點便是如此)。也因為這樣,在翻譯本書時,我和夥伴都得在保持原文狀態的情況下,用不影響內容的方式增譯,好比說為前後矛盾的內容加個轉折連接詞,或者加上一些簡單的補充、附註等。
以連接詞來舉例,其實有時候只是補上「舉例來說」、「不過」,就可以讓語句順暢、好懂許多。又或者是簡單補充符合文意的「後來」、「當時」,讓今昔對比、時間序等得以清楚呈現出來,不但不影響文意,還可以讓讀者更能了解時序。例如第八章有一句話我翻譯成:「施普倫格爾的結論違反了當時盛行的教條」,只要加入「當時」就能讓文具更通順,讀起來會比「施普倫格爾的結論違反了盛行的教條」還清楚。
有時則是需要補充作者沒有明講出來的言下之意。一樣以第八章來舉例。
作者原文:Illustrators may have to work with limited evidence, using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hen (re)arranging and reconstructing whole structures from fragmentary materials.
我的譯文:要從零散的材料(重新)排列和重建整株植物結構時,繪師可能只得仰賴有限的證據,利用他們的知識和經驗來完成任務。
仿間很多譯作看起來像是字對字的翻譯,但因為我的背景是口譯,我通常會用內容「容不容易被讀者/觀眾吸收」的方式來做判斷。在這個例子裡,如果句子只寫到「……繪師可能只得仰賴有限的證據,利用他們的知識和經驗」,若寫到這裡便結束,對讀者來說會有斷點,所以我在最後面加上「來完成任務」,這樣不但不影響文意,反而會讓意思更清楚,讀起來也更像真人的口吻,讓文字多了一份溫度。
書中的科學世界
以前教授常跟我們說,翻譯需要對原文保持警覺,也要時時刻刻意識到自己在說什麼、寫什麼。我選了上面的例句一方面是凸顯譯者在工作時真的需要字斟句酌,每一刻都要專注地判斷眼下的句子與前後文的關係、位處整篇文章的哪個架構、在整本書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想呈現書中縝密的研究給大家認識。
如同前述,小小的錯誤便能影響大局,時代的常備知識及氛圍也會影響研究者和繪師的主觀意識。作者對「植物科學繪畫史」的考究值得玩味,但也值得我們這個時代的研究者、知識工作者甚至政治工作者省思,畢竟「一切都是政治」(最近最流行也最真誠的一句話),無論學者或是藝術家,如果大家都懼怕提出異議,一昧順從時代的聲音,那麼科學、藝術便不會演進了。
最後插播,我在這本書中還學到另一件事:女性繪師對於植物插畫相當有貢獻。而女性藝術家由於在舊時代受到許多束縛,出門要有人伴行、能學習的繪畫及藝術種類也有限,植物插畫反而是女性容易接觸且能夠發揮一己之才的地方。這部分剛好和我最近在讀的歐洲女性藝術史不謀而合,等讀完書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囉。

最後一樣工商,如果有藝術史、文化史的書籍或出版品需要翻譯,或者藝術講座、研討會需要口譯,歡迎與我聯絡:ryeryelin [at] gmail.com
若對本書有興趣,也歡迎購書支持: